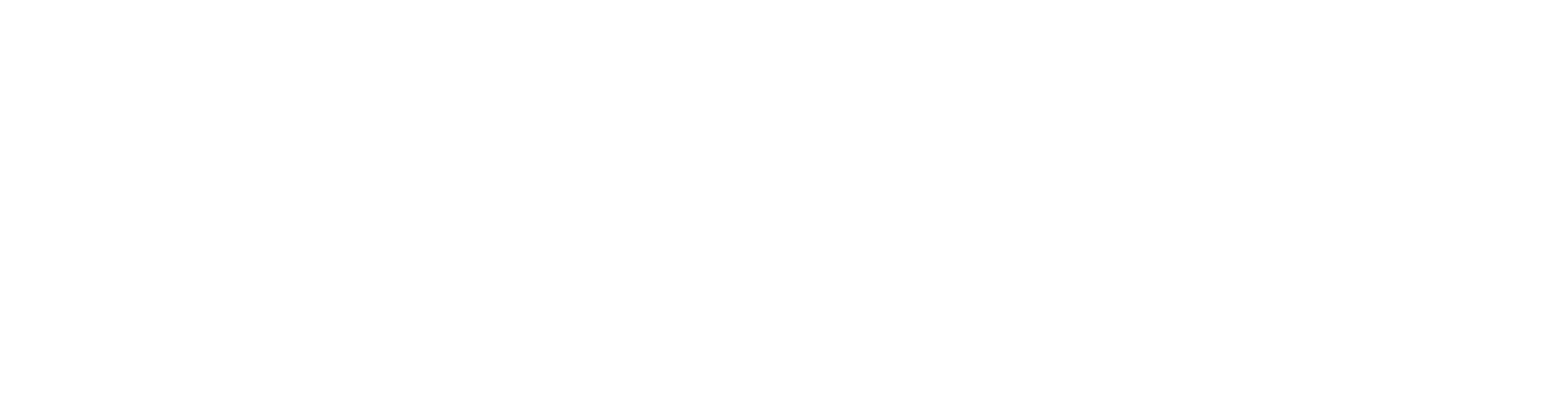白细胞介素 - 1α(IL-1α)作为白细胞介素 - 1(IL-1)细胞因子家族的核心成员,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生物学功能网络,包括调控炎症反应、免疫细胞活化、组织稳态及肿瘤微环境调节。IL-1α 兼具可溶性细胞因子和细胞内 “警报素” 的双重身份,独特地连接了细胞应激信号与系统性免疫应答。与同源分子 IL-1β 不同,IL-1α 在多种细胞中呈组成型表达,并通过前体和成熟两种形式发挥生物学效应,能够快速与 IL-1 受体(IL-1R)复合物结合,启动下游信号级联反应。IL-1α 的调控异常已被证实参与多种疾病的发病机制,包括自身免疫病、慢性炎症性疾病、心血管疾病及恶性肿瘤。近年来,靶向治疗手段的进展 —— 如单克隆抗体、可溶性受体拮抗剂及基因沉默策略 —— 凸显了 IL-1α 作为治疗靶点的潜力。本文全面阐述了 IL-1α 的分子特征、复杂的信号通路、其在疾病病理生理中依赖于环境的作用,以及转化医学研究的最新进展。通过整合现有知识与新兴见解,本文旨在为 IL-1α 介导的机制及治疗创新的未来研究提供基础框架。
人类 IL1A 基因定位于 2 号染色体 q14.1 区,编码由 271 个氨基酸组成的前体蛋白(pro-IL-1α),分子量约 31 kDa。该前体经过翻译后加工生成 17 kDa 的成熟形式,但与 IL-1β 不同 ——IL-1β 的激活主要依赖于炎症小体中 caspase-1 介导的切割 ——pro-IL-1α 展现出功能多样性:其未加工形式即保留生物学活性,并可被多种蛋白酶切割,包括中性粒细胞弹性蛋白酶、组织蛋白酶 G 及基质金属蛋白酶(MMPs),具体依赖于细胞环境。例如,在富含中性粒细胞的炎症灶中,弹性蛋白酶在 113 位氨基酸处切割 pro-IL-1α,释放成熟的 17 kDa IL-1α,后者易于分泌;相反,在细胞凋亡过程中,caspase-3 可能在其他位点切割 pro-IL-1α,生成具有独特亚细胞定位和活性的截短形式。
结构上,IL-1α 采用 β- 三叶折叠构象,这是 IL-1 家族的保守基序,由 12 条 β 链排列成三个反平行 β 片层。该折叠形成一个疏水口袋,对受体结合至关重要,关键残基(如 Arg41、Lys98 和 Glu105)介导与 IL-1 受体(IL-1R1)胞外域的相互作用。值得注意的是,pro-IL-1α 包含成熟形式所没有的 N 端结构域(1-112 位氨基酸),其中含有核定位序列(NLS)和染色质结合基序。这一独特结构特征使 pro-IL-1α 能够转运至细胞核,独立于受体信号调节基因转录 —— 这是其区别于大多数细胞因子的特性。
IL-1α 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在多种细胞类型中的组成型表达,这与 IL-1β 的诱导型表达形成鲜明对比。上皮细胞(包括皮肤、呼吸道和胃肠道黏膜上皮)维持基础水平的 pro-IL-1α 表达,作为屏障组织 “哨兵” 功能的一部分。例如,表皮角质形成细胞在细胞质和细胞核中储存 pro-IL-1α,参与角质形成细胞增殖和分化等稳态过程。微血管内皮细胞也组成型表达 pro-IL-1α,使其能够对血管损伤作出快速反应。
遍布全身结缔组织的成纤维细胞是 pro-IL-1α 的另一主要来源。在滑膜、肺间质和真皮等组织中,成纤维细胞持续分泌低水平 pro-IL-1α,通过与硫酸乙酰肝素蛋白聚糖的相互作用在细胞外基质(ECM)中积累。这种 ECM 封存形成 IL-1α 的 “储备池”,在组织损伤时释放,放大局部炎症反应。免疫细胞(包括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DC)和自然杀伤(NK)细胞)也表达 IL-1α,但其产生通常在炎症刺激(如脂多糖(LPS)、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或病毒核酸)作用下上调。
IL-1α 的生物学活性不限于其作为分泌型细胞因子的作用;它通过细胞内和细胞外机制发挥依赖于环境的效应,这一特性称为 “双重功能”。
细胞内 pro-IL-1α:在存活细胞中,pro-IL-1α 主要位于细胞质或细胞核。核内 pro-IL-1α 通过与染色质修饰因子(如组蛋白乙酰转移酶)和转录因子(如 NF-κB、p53)相互作用,充当转录调节因子。例如,在角质形成细胞中,核 pro-IL-1α 增强参与伤口再上皮化的基因(如角蛋白 16 和基质金属蛋白酶 - 1)表达。在癌细胞中,核 pro-IL-1α 可通过上调抗凋亡蛋白(如 Bcl-2)促进细胞存活,或通过激活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驱动增殖。
细胞外 IL-1α:pro-IL-1α 和成熟 IL-1α 均可释放到细胞外空间,通常在细胞损伤、坏死或主动分泌(与经典高尔基体介导的胞吐不同的过程)后发生。细胞外 IL-1α 通过由 IL-1R1(信号亚基)和 IL-1R 辅助蛋白(IL-1RAcP)组成的异二聚体受体复合物传递信号。IL-1α 与 IL-1R1 的结合诱导构象变化,招募 IL-1RAcP,触发下游信号级联反应,包括 NF-κB、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s:ERK1/2、JNK、p38)和磷脂酰肌醇 3 - 激酶(PI3K)/Akt 通路。这些通路共同驱动促炎细胞因子(IL-6、TNF-α)、趋化因子(CXCL8、CCL2)和黏附分子(ICAM-1、VCAM-1)的表达,放大炎症反应和免疫细胞募集。
IL-1α 被归类为 “警报素”—— 一类在细胞应激或损伤时释放的内源性分子,向免疫系统发出组织损伤警报。与应对外源性威胁的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MPs)不同,IL-1α 等警报素启动无菌性炎症,这一过程对组织修复至关重要,但失调时具有致病性。
细胞坏死是 IL-1α 释放的主要触发因素,因为膜完整性的丧失使细胞质和核 pro-IL-1α 泄漏到细胞外环境。相反,凋亡细胞通常由于膜 blebbing 和吞噬清除而保留 IL-1α,防止不适当的炎症。然而,在癌症或慢性感染中的不完全凋亡条件下,继发性坏死可能发生,导致 IL-1α 释放。机械创伤、氧化应激或化学损伤(如紫外线辐射)也通过破坏细胞膜或激活应激反应激酶(如 p38 MAPK)诱导 IL-1α 分泌。
释放后,IL-1α 作为 “第一反应者”,快速激活组织驻留免疫细胞(如巨噬细胞、肥大细胞)和基质细胞,启动炎症级联反应。这种警报素功能在屏障组织中尤为关键,它连接组织损伤与免疫监视 —— 例如,在皮肤中,晒伤角质形成细胞释放的 IL-1α 驱动中性粒细胞浸润并启动组织修复;在肺中,受损肺泡上皮细胞释放的 IL-1α 参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的早期炎症反应。
IL-1α 的生物学效应通过受体和拮抗剂网络严格调控,以防止过度炎症。主要信号受体 IL-1R1 是 I 型跨膜蛋白,其胞外区具有三个免疫球蛋白样结构域,胞质尾区含有 Toll/IL-1 受体(TIR)结构域。IL-1α 与 IL-1R1 结合后,诱导构象变化,使 IL-1RAcP 募集,使它们的 TIR 结构域接近,从而招募衔接蛋白(如 MyD88、IRAK4),传播下游信号。
负调控通过多种机制实现:
IL-1R2:一种缺乏功能性 TIR 结构域的诱饵受体,IL-1R2 以高亲和力结合 IL-1α,但不启动信号传导,将细胞因子与 IL-1R1 隔离。膜结合 IL-1R2 经蛋白水解切割产生的可溶性 IL-1R2(sIL-1R2)在全身循环,抑制 IL-1α 活性。
IL-1 受体拮抗剂(IL-1Ra):一种天然存在的蛋白质,与 IL-1α 竞争结合 IL-1R1 而不激活信号传导。IL-1Ra 由巨噬细胞、成纤维细胞和内皮细胞产生,在炎症期间其分泌上调,以限制细胞因子介导的组织损伤。
内吞作用与降解:IL-1α-IL-1R1-IL-1RAcP 复合物在受体激活后通过网格蛋白介导的内吞作用内化,导致 IL-1α 的溶酶体降解和受体再循环或降解,终止信号传导。
IL-1α 驱动持续性炎症的能力使其成为自身免疫和慢性炎症疾病的关键促成因素,其中自身组织损伤使警报素释放和免疫激活永久化。
在 RA 中,IL-1α 在受累关节的滑膜衬里中大量表达,主要由滑膜成纤维细胞(FLS)、巨噬细胞和软骨细胞产生。Pro-IL-1α 在滑膜 ECM 中积累,在那里被浸润的中性粒细胞和 FLS 分泌的 MMPs(如 MMP-9)切割成活性形式。细胞外 IL-1α 随后激活 FLS 分泌促炎细胞因子(IL-6、TNF-α)和基质降解酶(MMP-1、MMP-13),侵蚀关节软骨和骨。此外,IL-1α 上调 FLS 和成骨细胞上 RANKL(核因子 κB 受体活化因子配体)的表达,促进破骨细胞分化和骨吸收 —— 这是 RA 相关骨丢失的标志。
RA 小鼠模型研究表明,IL-1α 的基因缺失减少关节肿胀、软骨损伤和破骨细胞活性,即使在 IL-1β 信号完整的情况下也是如此,突显其非冗余作用。在人类中,滑膜 IL-1α 水平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血清 IL-1α 升高与对常规 DMARDs(改善病情抗风湿药)的不良反应相关,强调其作为治疗靶点的潜力。
银屑病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皮肤病,其特征是角质形成细胞过度增殖和 T 辅助 17(Th17)介导的炎症。IL-1α 在银屑病斑块中高度表达,从活化的角质形成细胞释放,参与致病级联的启动和维持。银屑病角质形成细胞中的 pro-IL-1α 在细胞核中积累,驱动与过度增殖(如细胞周期蛋白 D1)和趋化因子产生(如 CXCL8、CCL20)相关的基因表达。从受损角质形成细胞释放的细胞外 IL-1α 激活树突状细胞分泌 IL-23,这是促进 Th17 细胞分化和 IL-17 产生的关键细胞因子 ——IL-17 反过来进一步刺激角质形成细胞分泌 IL-1α,形成致病前馈循环。
使用 IL-1α 中和抗体的银屑病小鼠模型研究表明,表皮增厚、中性粒细胞浸润和 Th17 细胞因子表达减少。临床数据也支持这一联系:银屑病患者病变皮肤和血清中 IL-1α 水平升高,IL-1α 多态性(如 rs17561)与疾病易感性增加相关。这些发现将 IL-1α 定位为银屑病炎症的关键介质,不同于在这种情况下作用较小的 IL-1β。
IL-1α 通过促进血管炎症、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肌损伤,参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机制。
动脉粥样硬化是动脉壁的慢性炎症性疾病,由高血压、高脂血症和吸烟等危险因素引起的内皮功能障碍引发。受损内皮细胞释放 IL-1α,上调黏附分子(ICAM-1、VCAM-1)和趋化因子(CCL2)的表达,将单核细胞募集到内皮下空间。这些细胞分化为巨噬细胞后,内化氧化低密度脂蛋白(oxLDL)形成泡沫细胞,分泌额外的 IL-1α,放大局部炎症。
IL-1α 还通过刺激平滑肌细胞(SMC)从中膜增殖和迁移至内膜,促进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进展,有助于纤维帽形成。然而,在晚期斑块中,IL-1α 通过激活巨噬细胞中的 MMPs(如 MMP-9)促进斑块不稳定,MMPs 降解纤维帽并增加破裂风险。临床研究支持这一作用:IL-1α 在人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高度表达,特别是在不稳定区域,血清 IL-1α 水平可预测冠心病患者的心血管事件。尽管 CANTOS 试验聚焦于 IL-1β,但抗 IL-1 治疗减少复发性心血管事件的发现激发了对 IL-1α 特异性靶向的兴趣。
MI 后,缺血心肌细胞发生坏死,向心肌释放大量 IL-1α。这种警报素触发急性炎症反应,其特征是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浸润,这对于清除死亡细胞是必要的,但如果延长则会加剧组织损伤。IL-1α 激活心脏成纤维细胞分泌促炎细胞因子(IL-6、TNF-α)和促纤维化因子(TGF-β),参与梗死后纤维化和心室重构。
MI 小鼠模型中,IL-1α 缺乏减少梗死面积,改善左心室功能,并减少纤维化,而重组 IL-1α 给药恶化结果。在人类中,MI 后 24 小时内血清 IL-1α 水平升高与更大的梗死面积和心室恢复不良相关。这些数据表明 IL-1α 是缺血后心肌炎症的关键介质,使其成为限制 MI 后心脏损伤的潜在靶点。
IL-1α 在癌症中发挥依赖于环境的作用,根据癌症类型和微环境,既作为肿瘤促进因子,在某些情况下也作为免疫激活因子。
在许多实体瘤中,IL-1α 由癌细胞、基质细胞(如 CAFs)或浸润免疫细胞过表达,促进肿瘤生长、血管生成和转移。
血管生成:IL-1α 刺激肿瘤相关内皮细胞和 CAFs 分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2(FGF2)和血管生成素 - 2,促进异常肿瘤血管的形成。例如,在结直肠癌(CRC)中,癌细胞释放的 IL-1α 上调 CAFs 中 VEGF 的表达,增强微血管密度和肿瘤灌注。
免疫抑制:IL-1α 通过诱导趋化因子如 CXCL8 和 CCL2 募集免疫抑制细胞,如髓系来源抑制细胞(MDSCs)和 M2 极化巨噬细胞。这些细胞通过精氨酸酶 - 1、吲哚胺 2,3 - 双加氧酶(IDO)和活性氧(ROS)抑制抗肿瘤 T 细胞反应。在胰腺导管腺癌(PDAC)中,癌细胞的 IL-1α 驱动 MDSC 积累,创造限制免疫治疗 efficacy 的免疫沙漠。
转移:IL-1α 通过上调 Snail 和 Twist(减少 E - 钙粘蛋白表达并增强细胞运动性的转录因子)促进癌细胞的上皮 - 间质转化(EMT)。在乳腺癌中,原发肿瘤分泌的 IL-1α 通过激活基质成纤维细胞和改变细胞外基质以支持癌细胞定植,使远处器官(如肺、骨)为转移做好准备。
与肿瘤促进作用相反,IL-1α 在某些情况下可增强抗肿瘤免疫。例如,在黑色素瘤中,从垂死癌细胞(化疗或放疗后)释放的 IL-1α 作为警报素激活树突状细胞,促进其成熟和向 CD8⁺ T 细胞呈递抗原。这一过程称为 “免疫原性细胞死亡”,增强 T 细胞浸润并改善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的反应。临床前研究表明,放疗与 IL-1α 激动剂联合使用增加小鼠黑色素瘤模型中的肿瘤浸润性 CD8⁺ T 细胞并减少肿瘤生长。
此外,IL-1α 可与其他细胞因子协同增强抗肿瘤免疫。在结直肠癌中,IL-1α 上调 CXCL9 和 CXCL10 的表达 —— 这些趋化因子招募 CXCR3⁺效应 T 细胞;在膀胱癌中,IL-1α 增强 NK 细胞产生 IFN-γ,促进癌细胞裂解。这些发现突显了 IL-1α 在癌症中的背景依赖性,强调了靶向方法的个性化需求。
IL-1α 在感染中发挥双重作用:对控制病原体至关重要,但可在脓毒症中驱动危及生命的炎症。
在细菌感染中,IL-1α 从受感染或受损宿主细胞释放,招募中性粒细胞并激活巨噬细胞,增强吞噬作用和细菌清除。例如,在肺炎球菌肺炎中,肺泡上皮细胞的 IL-1α 驱动中性粒细胞浸润到肺部,这对清除肺炎链球菌至关重要。同样,在尿路感染(UTIs)中,膀胱上皮细胞的 IL-1α 激活先天免疫反应以消除尿路致病性大肠杆菌。
然而,在严重感染中,IL-1α 的过度释放可导致脓毒症 —— 以低血压、器官衰竭和凝血病为特征的失调全身性炎症反应。在脓毒症中,细菌 PAMPs(如 LPS)和宿主 DAMPs(如 IL-1α)协同激活巨噬细胞和内皮细胞,导致 “细胞因子风暴”,产生高水平的 IL-1α、TNF-α 和 IL-6。这压倒了稳态机制,导致血管渗漏、组织低灌注和多器官功能障碍。脓毒症动物模型表明,IL-1α 中和降低死亡率、器官损伤和促炎细胞因子水平,表明其与 IL-1β 一起是脓毒症病理的关键驱动因素。
抗 IL-1α 单克隆抗体(mAbs)代表最先进的靶向治疗类别,旨在阻断 IL-1α 与 IL-1R1 的结合。
Xilonix(gevokizumab):一种人源化 IgG1 mAb,以高特异性结合 IL-1α(Kd≈1 pM)并阻止受体激活。晚期结直肠癌的 II 期试验(NCT03207802)表明,Xilonix 与标准化疗联合使用将疾病控制率(DCR)从 45% 提高到 68%,并将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延长 2.3 个月。机制研究将这些效果归因于肿瘤中 MDSC 浸润减少和 CD8⁺ T 细胞密度增加。在癌症恶病质(一种非自愿体重减轻综合征)中,Xilonix 通过抑制 IL-1α 介导的骨骼肌蛋白水解减少临床前模型中的肌肉消耗,II 期试验(NCT02401951)显示晚期胰腺癌患者体重减轻减少 30%。
银屑病中的抗 IL-1α mAbs:一项评估新型 IL-1α mAb 在中重度银屑病中的 I/II 期试验(NCT04021082)报告,12 周后 62% 的患者银屑病面积和严重程度指数(PASI)评分降低 50%,无严重不良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反应维持长达 24 周,表明持久疗效。
Anakinra 是 IL-1Ra 的重组形式,被批准用于治疗自身炎症性疾病(如冷吡啉相关周期性综合征),通过阻断 IL-1α 和 IL-1β 与 IL-1R1 的结合发挥作用。虽然对 IL-1α 的特异性较低,但 Anakinra 在 IL-1α 驱动的疾病的标签外使用中显示出前景。例如,在一小群难治性 RA 患者中,Anakinra 减少关节炎症并改善身体功能,应答者表现出更高的基线 IL-1α 水平。在 MI 后患者中,24 小时内给予 Anakinra 减少全身炎症(通过 C 反应蛋白测量)并在 6 个月时改善左心室射血分数,尽管需要更大规模的试验来证实这些效果。
RNA 干扰(RNAi)和反义寡核苷酸(ASOs)提供了沉默 IL1A 表达的新方法。使用脂质纳米颗粒(LNP)封装的靶向 IL1A 的 siRNA 的临床前研究在 RA 小鼠模型中显示 IL-1α 水平降低 > 80%,同时关节炎症和骨侵蚀相应减少。最近的一项研究(Nature Nanotechnology, 2023)报道,与靶向 CAFs 的肽偶联的 LNP-siRNA 在肿瘤基质中实现 90% 的 IL1A 沉默,减少血管生成并抑制 CRC 异种移植物中的肿瘤生长。这些靶向递送系统最大限度地减少脱靶效应,解决了早期 RNAi 疗法的关键限制。
尽管取得了进展,仍存在若干挑战:
组织特异性靶向:IL-1α 的全身抑制可能破坏其在组织修复中的生理作用,增加感染风险。例如,Anakinra 与 2-3% 的严重感染发生率相关,强调对细胞或组织特异性递送系统的需求。
背景依赖性:IL-1α 在癌症中的双重作用(促进剂 vs 激活剂)需要生物标志物来识别最可能受益的患者。血清 IL-1α 水平、肿瘤 IL1A mRNA 表达和遗传多态性(如 rs17561)正在作为预测标志物进行评估。
联合策略:鉴于 IL-1α 在免疫抑制中的作用,将 IL-1α 抑制剂与 ICIs(如抗 PD-1)联合使用可能增强应答。黑色素瘤的临床前研究表明,抗 IL-1α + 抗 PD-1 将肿瘤消退率从 35% 提高到 72%,通过逆转 T 细胞耗竭。
确定可靠的生物标志物对于分层可能对 IL-1α 靶向治疗有应答的患者至关重要。有前景的候选者包括:
血清 IL-1α 水平:基线水平升高与 CRC 和银屑病中 Xilonix 的应答相关。
IL1A 基因多态性:与 IL-1α 产生增加相关的 rs17561 G 等位基因预测乳腺癌预后不良,并可能识别受益于 IL-1α 抑制的患者。
肿瘤微环境特征:高 IL-1α 表达结合低 PD-L1 可能表明对抗 IL-1α + 抗 PD-1 联合治疗的敏感性。
纳米技术为细胞特异性 IL-1α 抑制提供了解决方案。例如:
CAF 靶向纳米颗粒:与成纤维细胞活化蛋白(FAP)抗体偶联的脂质体可将 IL-1α siRNA 特异性递送至 CAFs,减少肿瘤基质中的 IL-1α 而不影响正常组织。
pH 敏感纳米颗粒:这些系统在酸性肿瘤微环境(pH 6.5-6.8)中释放 IL-1α 拮抗剂,最大限度地减少全身暴露。
新兴证据支持 IL-1α 靶向在以下方面的应用:
神经退行性疾病:活化小胶质细胞释放的 IL-1α 促进阿尔茨海默病中的神经炎症;临床前研究显示 IL-1α 抑制减少淀粉样蛋白沉积和认知下降。
慢性肾病(CKD):IL-1α 驱动 CKD 中的肾小管间质炎症和纤维化,Anakinra 在糖尿病肾病患者的小型试验中改善肾小球滤过率(GFR)。
IL-1α 作为具有警报素特性的多功能细胞因子,在多种疾病的发病机制中占据核心地位,从自身免疫到癌症。其独特特征 —— 组成型表达、细胞内 / 细胞外双重活性以及作为损伤传感器的作用 —— 使其区别于其他 IL-1 家族成员,并强调其作为治疗靶点的潜力。尽管存在挑战,包括背景依赖性作用和递送问题,但单克隆抗体、基因沉默技术和精准医学的进展正在迅速扩展我们利用 IL-1α 抑制进行临床获益的能力。随着我们对 IL-1α 介导机制的理解加深,它有望成为炎症驱动疾病治疗的基石。